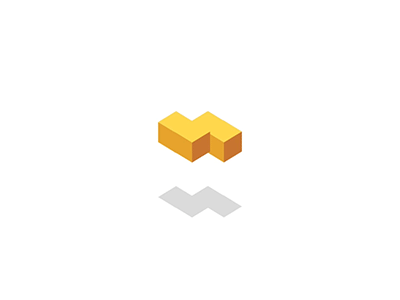摘 要:法治在当代中国成了一个重要的时代性命题 。 但是,目前的相关研究,过分的侧重于对西方制度的介绍,对中国法治本土资源的挖掘还远远不够 。 诚如着名人类学家吉尔兹( Clifford Geertz) 所言,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 当代的法律世界是一个多元性体系,中国法律文化在其中也应当有其独特的地位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顾梁治平先生提出的法律文化论有特殊的价值 。 而且,法律文化论实际上亦是一个永远不会终结的话题 。
关键词:梁治平; 法律文化论; 自然秩序中的和谐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似乎一度成为非常时髦的话语 。 而梁治平先生提出法律文化论,虽然不是出于赶时髦的目的,但是毕竟身处文化热的大背景下,不能不受其感染 。 梁先生在《读书》上连续发表了十余篇涉猎广泛而主题与方法却相当一致的文章,这十余篇文笔清新的文章与 1986 年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上那篇着名的论文《法辨》一起构成了梁先生法律文化论的基本论题 。 这些起初还略显朦胧的论述在后来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及整理,而该书的副题即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 。 前述的那些文章和该书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法律文化图式,它们无论是在研究的内容还是方法上,都是法律史研究方面的新突破,其开阔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视野,实际上也提升了这种研究的学术价值 。 当然,梁先生自己更注重的是他所提倡的方法论,所以后来又有了《法律的文化解释》一文的撰写与同名着作的编辑 。 梁先生对方法论的提倡自然有其道理,因为对学术方法的强调可以让研究不至于停滞在一个特定的结论,因而更能推动特定研究范式的延续 。
一、法律文化论的概念体系
在这里先以《和谐》一书为中心谈谈法律文化论 。 其实,单从这本着作的标题就可以看出梁先生法律文化论的一些端倪 。 作者对中国法律文化的核心归纳为自然秩序中的和谐,这确实十分到位,甚至可以说是恰到好处,因为儒家与道家的并存和互补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特征 。 儒家的礼和道家的道,都是一种自然秩序,当然儒家的礼是一种血缘的自然秩序,是伦理化了的人间的自然秩序,而道家的道则形而上的色彩更浓,因而可以说是神秘的自然秩序 。 而自然秩序的根本特征则是和谐,和谐的,即是自然的,即是符合中国文化审美情致和道德判断的 。
这种自然而然的平衡状态( 和谐) 需要德礼和刑政二个不同方面的合作才能得到最终的维系,而德礼的方法是教,刑政的方法是法 。 教是从积极的方面出发去促进和谐因素,法是从消极的方面出发去消除不和谐因素 。 先秦时期有过儒家与法家的着名争论,儒家主张以教来化成天下,而法家主张以法来胁服人心,两者的观点乍一看颇相抵牾,可是梁先生以治乱之道的标题,将它们纳入了一个共同的范畴之下,而治乱之道正是该书第三章的标题,作者在开篇即引用了《史记太史公自序》里纵论六家要旨的名言: 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 梁先生敏锐地发现了太史公这一个治字的分量,它抹去了先秦诸子百家表面上的对立,而表明了中国文化内在的高度统一 。 因此,梁先生认为儒法两家在畅论不同的治道之时,实际上是以更大程度上的共识作为前提 。 这种共识是它们关于法的观念,是它们关于君主权威以及等差秩序的看法 。
总之,儒家和法家的争论,只是工具( 方法) 论的争论,没有涉及到价值论的层面 。 因此,它们保留了一种合流的可能性 。 这种儒法合流的混合形态是礼法文化( 该书第九章的标题) ,礼法文化的特征是道德的法律化( 该书第十章的标题) 和法律的道德化( 该书第十一章的标题) 。 当然,关于儒法合流( 即外儒内法) 以后,儒家和法家的地位如何,则尚有一番曲折,儒家主导论是目前的 通说 。 因为,后世用以概括汉武帝崇儒的那句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国人心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 但是,余英时先生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却表达了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看法,余先生以为儒家在汉武帝时期不过是扮演了文饰的作用,未必有后人说起来的那么显赫 。 因此,儒家只是在宋代( 尤其是南宋后期) 之后才真的实现文化上的独尊,之前则似乎未必 。
总之,梁先生用的礼法文化一词,确实是对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极好的概括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礼法文化中的法是一种中国意义上的概念,只能从文化人类学的意义上将它与现代法治中的法的概念相类比 。 因为,礼法中的法只是单纯的惩罚准则,它没有独立的规范品格 。 西方的法,即使是在它的文明早期,也有着它的规范品格 。 西方法律的规范品格体现为: 作为个体的权利,作为普遍的正义 。 正因为它既可以是权利的分配和矫正机制,又存在二元结构的对立,所以它最终能够被认定为社会秩序的基础 。 因为,它作为权利的分配和矫正机制可以中立地裁决社会中的争端,因而获得了一种非单纯暴力压迫的性质,同时,又因为它承认权利的合理性,所以又得到了一种普遍的信赖,这样私法才有了形成和发展的可能 。 而它作为普遍的正义,就导致了上述的二元对立结构,这是一种法与法律的对立,②前者表现为自然法传统,后者表现为实证法传统(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中,法与法律的概念区别,得到了成文宪法的承认) 。 自然法对实证法的批判,保障了实证法的正当性基础 。 同时,自然法本身的抽象性,又具有了一种时代的包容性,因此可以有古希腊智者的自然法、斯多噶学派的自然法、古罗马的万民法、中世纪的自然法、古典自然法和现代的新自然法 。 这种时代的包容性使自然法获得了一种独立的理论品质,它的内容虽然前后殊异,但作为一种理论模式却贯穿古今,使得每一个时代的正义精神都有所寄托,并依此起到批判并改善实证法的作用 。
与西方自然法传统不同,决定中国法律规范品格的是礼,而礼是身份和伦理的秩序,这种秩序强调的是自然的和谐,它否定了个人权利的合理性( 因为基于权利的主张在中国古人看来是一种争利之心,它本来就是对和谐的破坏) ,强调了相互之间的义务 。 同时,因为礼本身是抽象道德精神和具体仪节细则的结合体,它也无法构成二元对立结构,也就无法构成对实证法的批判,因为它一方面已经以礼入法地影响了法律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在不应得为罪这种中国古代法律特有的罪名那里直接转化为了实证法本身 。 而且,因为法律并没有规范品格,所以其实也没有批判的必要 。 这种自然法传统与礼法文化的对比,构成了本书的第十二章《自然法》 。 其实,《和谐》全书都贯穿着比较法( 辨异) 的方法,而这一章则是更为纯粹和全面的比较,因为它是在全书接近尾声并已经作出总结( 第九到十一章是总结部分) 的情况下作出的比较 。 作为本书结尾的第十三章转捩点: 过去与未来则是以清末的法律改革作为中国法律史的转捩点,梁先生认为从此中国法律的问题就是现代化的问题,而古老的中国法律传统( 但并不是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 则已经成为过去 。 这在本章的最后一句话里得到了总结: 作为旧秩序的古代文明已然死去,要紧的是,我们还可能去建设一个新的文明,这便是希望所在 。 20 年代前后的中国,就是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捩点上 。
二、法律文化论的方法论
笔者在这里是直接提出了梁先生法律文化论的结论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与礼法文化,而没有回顾这种结论的提炼过程 。 因为,很多读者可能都会持这样一种看法: 没有哪种文化是一诞生就带有了某种先验的性格特征,一切都是历史形成的,它的过程决定了它的性质 。 这种看法自然是有道理的,而梁先生的《和谐》一书本身就是对这种过程的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梁先生还强调了人类文明早期经验的特殊重要性,他所持的并不是简单的流水账式的过程论) 。 而笔者之所以暂时搁置了对这个过程的回顾,是因为它本身还有着另外一种特殊的意义,即这个历史考察的过程其实就是梁先生运用他的方法论的过程,所以有单独讨论的必要 。 这种冷静而理性的方法论虽然目前反响似乎并不十分热烈,但也许比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与礼法文化的结论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 。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梁先生方法论的对象虽然是历史,但不是那种纠缠于细节的历史,依梁先生自己的说法则是黄仁宇笔下的那种大历史 。 因为梁先生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求中国法律传统的精神,而不是对法律史进行历史的梳理 。 当然,这与梁先生的研究兴趣有关,他所希冀的也是成为一个思想型学者,而非专家型学者 。 如果在一段历史上徘徊过久,梁先生势必会失去思考的自由性,虽然他的思考从未完全游离于历史之外,但也总与历史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 。 姑且把梁先生的研究取径称作历史性思考吧 。
梁先生的方法论主要是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尤其是其中的后半句用文化去阐明法律 。 从一个作为整体的文化传统来理解作为分支的法律传统,且运用了文化类型学的方法,这最早在《比较法与比较文化》一文得到提倡,又在《法辨》那里得到了运用,同时《法辨》又在辨异的过程中尝试了语言分析的方法,这些方法后来都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得到了综合性运用 。 该书的第一章到第八章是分析的过程,也就是前文故意暂时性略过的部分 。 它们的章节名分别是: 家与国刑法律治乱之道《法经》与《十二表法》个人阶级义利之辨无讼 。 从这些章节名中显然可以看到《法辨》中的语言分析方法的延续 。 至于辨异的方法则贯穿于全书每一个章节,以上述八个章节而言,则尤以第四章《法经》与《十二表法》为代表,是一个直接以比较法律史为题目的章节 。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辨异,在梁先生收入《法辨: 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一书中的那些早期论文多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而且这种批判往往是以西方的法律传统作为标准进行的 。 这种批判意识在《和谐》里得到了淡化,《和谐》一书里更多的是比较冷静的学术反思,不过否定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态度并没有改变 。 虽然,作者在《法辨》这本论文集的后记中提到,在他写作《和谐》时渐渐地产生了一种同情的理解,但是我们在该书中实际上找不到这种所谓的同情的理解 。 因为完成于 1988 年的《和谐》一书有它特殊的时代背景,在以中西对比为主题的文化热的潮流下,其实蕴含的是对西方文化的无限向往,这对于刚刚步入开放时代的中国而言,实在也是无可厚非的 。 情势如斯,该书尚能提出同情的理解的主张,已属难得 。
另一个应该注意的地方是,《和谐》一书中有一个文化基因论的假定,关于此点笔者在前文中已经稍微提及,而且实际上这种理论倾向在《法辨》那里就已经比较明显了 。 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基因论的假定,梁先生特别注重中国文化的早期经验,这也是张光直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在该书中得到频频引用的原因 。 同时,这种文化基因论也决定了梁先生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的解释方法的一些特色,那就是以作为整体的文化( 而这种文化的性格孕育于早期文明) 来解释法律问题,同时以法律的历史来验证这种解释,这种阐明的过程在早期文明那里徘徊得相对较久,而在各个具体朝代则只是轻轻掠过 。 因为从文化基因论的观点看来,只有人类早期的经验才是最为根本的 。 在梁先生看来,早期国家和法律形成的特殊经验已经决定了历史的大方向,比如家国同构和法律的刑事属性,其中又引出了一系列的后续问题,比如家族制度的影响导致个人的不彰,法律的刑事属性决定了它不能成为一种公认的社会秩序基础,等等 。 其实,正是梁先生的这种早期经验决定论的观点才使得他的大历史有了可能性,否则很难不陷入历史繁复的沼泽之中,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历史的落脚点青铜时代,在这个点上梁先生可以从容不迫地思考 。 当然黄仁宇先生选择的则是其他历史的落脚点,比如万历十五年( 黄先生对该年份的英文表述是1587,A Year of NoSignificance) ,可见历史的落脚点并不只有一处 。 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有这么一个点,以这个点来追溯它的上游和下游,厘清历史的脉络 。
三、《法律的文化解释》:法律文化论的范式转型
这篇文章是梁先生对自己方法论的事后总结和继续深化 。 但邓正来先生以其犀利的眼光发现了梁先生法律文化论前后之间的多处紧张和矛盾 。 考虑到梁先生自己曾指出他并没有构建理论体系的想法,甚至不觉得有必要这样去做,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过分地苛求梁先生的前后一致性 。 没有体系性也有它的好处,那就是保留了更多的思考自由,而不用害怕挂一漏万或自我封闭 。 但是又顾及到《法律的文化解释》与之前研究的割裂性实在太明显了,所以笔者以为把它单独提出分析还是很有必要的,至于它所提出的新理念也未必就完全替代了之前的研究,恰恰相反,它只是出现在了先前研究成果的旁边,相当于多了一条路径,喜欢何者就由读者自己去选择 。 当然,考虑到邓正来先生对梁先生的特别期待,他指出梁先生法律文化论的那些前后紧张和矛盾则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不过在此则不能一一讨论了,读者可以直接去阅读邓先生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续) : 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 。
诚如邓正来先生指出的那样,《法律的文化解释》事实上确实对梁先生自己之前的理念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否定 。 因为《和谐》主要还是辨异的,辨异的目的和结果则是否定中国法律传统,而《解释》一文则强调了各种文化的自身合理性,主张以主观意义追寻的方法去追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秩序安排观念 。 《解释》一文受到了文化人类学和哲学解释学的甚多影响,它所关注的已经不再是客观的功能主义的法律文化,而是主观的意义主义的法律文化,或者说它所关注的只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具体而微的生命状态 。 这种观念的变化,使得作者能够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语境下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同情的理解,这正是《解释》一文与先前着述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缝 。 而梁先生自己却试图用《和谐》的再版前言来事后修补之,并把同情的理解表述为文化类型式辨异的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不过,这种修补又被邓正来先生察觉了,邓先生还郑重指出这种事后解释的前言很有可能会误导后来的读者 。 从中可以看出在文化热逐渐消退后,梁治平先生也趋于用更理性,或者说用真正的同情的理解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法律文化的问题,并对先前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修正 。 诚如苏力先生所言,梁治平先生以批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目的而辨异,但辨异又以理解传统为前提,所以这种辨异具有超出他主观设定的学术意义,是辨异引导梁治平先生走上了一条也许他起初并不准备走的路 。
梁先生的另一本重要着作《清代习惯法: 社会与国家》则转向了法律文化的小传统研究[7],主要是一种法社会学的研究 。 作者在书中提到了明清的社会变化以及它给法律带来的影响,这仍然是用文化去阐明法律的研究方法,不过,其离开了以前文化类型学辨异的范式( 虽然仍然还有少量的概念辨异) ,而深入了中国法律文化自身的考察 。 梁先生认为在明清之际,大传统无法为当时的现实提供一种法律机制,才有了民间秩序的自我生成,以填补存在的秩序真空 。 《清代习惯法》一书事实上形成了与《和谐》的对应关系,这两本书分别研究了中国法律文化的大、小传统 。 同时,《清代习惯法》的研究目标主要在于脱离国家法的单边框架,深入地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在梁先生看来恰恰是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核心 。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实际上也是同情的理解的方法的一次比较系统的运用 。
四、结语
梁治平先生的《法律的文化解释》与《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的再版前言为法律史研究树立了一种良好的典范,若能依此道路不断深化专题式研究,无论是对知识性考古式的事实还原,还是对法律史的理论解释都颇具价值 。 更为重要的是,它对建立中国法律文化的自信也会产生不可估量的意义:只有回到中国法律传统的自身逻辑之中,才能真正进入传统的思维世界,并体察到传统的合理性,而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新起点 。 由此出发,亦终将找到法律重建的文化基础 。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M].北京: 三联书店,2006: 189-215.
[2]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87-99.
[3]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82.
[4] 梁治平.在边缘处思考[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10: 235.
[5]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续) : 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J].政法论坛,2005,( 4) : 19-24.
[6] 苏力.批评与自恋[M].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4: 45.
[7]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 社会与国家[M].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1.